“决定”还是“接受”? 2024 Week 49 回顾
Contents
“人在重塑工具,而工具也在塑造人。”
——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
前两天重装了系统,有个观察:当系统反应有一秒钟的延迟时,我会感到烦躁;但我却愿意花一整天时间来读小说。我会对不经我允许就安装的软件十分反感,不卸载它们不罢休。这些看似是简单情绪反应,但其实不然。
仔细观察这些日常行为,能看到一些有趣的模式。重装系统时,想要的不仅仅是性能,还有对环境的掌控。而花时间配置各种工具,其实是在打造能够尽可能发挥而非阻碍能力的工作环境。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在手”的概念:最好的工具应该如同空气一般,在使用过程中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熟练的木匠拿着一把用惯了的锤子。提出了“普适计算”的计算机科学家 Mark Weiser 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最深刻的技术是那些消失的技术,它们溶解在日常生活中,直到与生活难以区分。
尼古拉斯·卡尔在他的那本《浅薄》中认为,我们和工具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木匠把锤子拿在手中的时候,他用手能做的只有锤子能做的事情,手变成了钉钉子和拔钉子的工具。
我们和工具在相互塑造。尼采使用打字机的经历就是个例子。他在开始使用打字机后,开始认为打字机是个“像我一样的东西”,还感到自己正在变成像它一样的东西——他认为,他的打字机正在参与塑造他的思想。
麦克卢汉在《理解传媒》中写,我们的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最终就会“麻木”。当我们用人工方式延展我们自身的某些部分时,我们同时也在让自己远离那个被增强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所具有的自然技能。为了利用技术的力量,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疏离。即便是像地图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简单的工具时,同样也会产生麻木效应;而使用智力技术的时候,代价尤其高昂。
今天建立在智能手机基础上的各种工具,在增强我们的能力方面,似乎没有比在让我们变得麻木方面更强。它们让我们更容易地自我催眠,以达到今天我们可能称之为“拖延”或“发呆”的状态。诺伦·格尔茨在《虚无主义与技术》中说,我们认为这种催眠不仅令人愉快,还很正当。这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筋疲力尽后所能享受的仅剩不多的特权。
或者说,对自主权的丧失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反抗——尽管是以近乎自残的方式。
电脑软件的延迟之所以令人烦躁,不是因为那短暂的等待本身,而是因为这种等待是被迫的,是对时间自主权的剥夺。同样,系统偷偷安装软件让人反感,是因为它侵犯了我作为计算机用户的决策权,打破了我对个人空间的掌控。
这种对自主权的追求,在工具使用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什么有人(就像我)愿意投入时间学习和配置 Vim 这样的上世纪的编辑器,而不是随便用用 Word 或者 VS Code 就好?这不是效率问题,这是自主问题——而当我们被压榨到除了刷短视频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们看似自主,但其实已经被困进了罗网之中。
如何逃脱这种无处不在的、满是诱惑的控制?我们需要一个思维框架。
倪考梦在《自主论》中提出的“自主三角形”理论认为,要做到自主,需要意愿、能力与资源,三者缺一不可。
这个框架很有帮助。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明确定义问题。身在局中,不见全局,就只能问出错的问题。
这个框架让我们得以在现今这样的不确定性时代中有机会保持自主。在不确定性面前,我们不仅要追求抗风险能力,还要培养从混乱中获益的能力。我们需要理解自己,需要尝试,需要拓展自己的边界,需要建立稳定又灵活的系统,再持续优化它。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元能力优先。与其投资于特定学科或领域,不如投资于学习和适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洞察力、迁移已有经验的能力,以及持续优化的反思能力。
人工智能革命已经发生两年了。机遇很多,挑战更大。它会大大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但也正在削弱人们的自主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将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课题。
最终,生活的艺术在于建立平衡的关系。这种平衡既包括效率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也包括专精和通用之间的平衡,更包括自主和控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做与自主有关的选择。
而自主,差不多是我们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本周的成果
- 重装了系统
- 完成了一项限时任务
- 开始使用新工具
本周的改变
- 好像不再继续长胖了
- 了解了一些流程和规则
- 对一些配置更了解了一些
做得还不错
- 没有头痛
- 效率还可以
- 有一些新的想法
做得不太好
- 作息有点乱
- 特定的任务有点拖延
- 没有及时更新信息导致有点手忙脚乱
下周的目标
- 早睡早起
- 增加运动量
- 保持学习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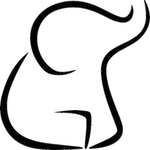 人生玩家
人生玩家